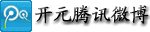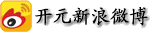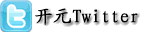日志
【散客月下欧洲灵异故事】 喀秋莎
||
鹰有时飞得比鸡低,但是鸡永远飞不了鹰那么高!
一进入阿尔巴特街,就听到街边一家店铺飘出一段熟悉的旋律,顿住脚步,侧耳聆听,不错,是《喀秋莎》。
到莫斯科已经半个月了,电视电台播放的都是流行音乐,听到的苏联歌曲,着实很感动。
《喀秋莎》是属于我父亲的歌声,我童年最美好的记忆是父亲骑着自行车带我进城,那样的日子很难得,一是作为空军干部,在文革那样剑拔弩张的岁月里,星期天不值班,很难得,二是,恰巧那天我爸爸心情好,我才能赢得这样的快乐。
机场到市区有很长一段乡村路,父亲边踩车边唱歌,而且,一支歌曲居然会唱了一遍又一遍。是那首歌翻来覆去地歌儿就是《喀秋莎》。
每次,我都会被告诫,不可以告诉别人他唱了这首歌。
那时候苏联这个国家被称为“苏修”,唱苏修歌曲,是绝对的叛逆行为。
如今,“苏修”这个词消亡了,苏联这个国家也解体了,我终于踏上父亲曾经踏过的土地,在我神往已久的阿尔巴特街头,听见了《喀秋莎》。
阿尔巴特街是莫斯科一条俄罗斯风格浓郁的历史老街,路面砖石铺设,两旁的古建筑简洁稳重而不奢华,店铺大多是书店画廊古玩铺。苏联解体前,我第一次读到了另类的苏联小说《阿尔巴特街的儿女》,小说展示了一个与父亲口中所描述的截然不同的苏联,更令我向往。
播放《喀秋莎》的铺子是一家旧货店,里堆满了各种雕花的金属器皿,圣像、珠宝首饰和传统服装,与中国古玩店比较,最大的区别是没有灰尘,每一件艺术品都被擦得干干净净。播放《喀秋莎》的是一台老式唱机,放黑胶唱片那种。
老板是个小老头,只是在巍峨进门时抬头看了我一眼,然后便把目光转回手中一本书上。
很奇怪,从进店开始,我一直觉得有一双眼睛在寸步不离地盯着我看,不是来自老那看书的老头, 那目光来自屋角,照不到的角落,有一双蓝灰色的眼睛。
一个女孩端坐钢琴前面,全身赤裸,身材丰满匀称,眼眸中流泻出青春少女特有的热情。
钢琴上赫然蹲着一只老鹰。
耳畔回旋这《喀秋莎》的歌词——“姑娘唱着美妙的歌曲,她在歌唱草原的雄鹰……”
她,一定就是喀秋莎!一定是的……虽然,她只是一幅油画。
我知道,油画是俄罗斯的经典艺术,莫斯科的物价高,油画也不便宜,据说一般都要价超过一千美元。
我决心买下这幅画儿,无论花多少钱。
实际上,老板开价大出我意料,我花了不到五百元,就把喀秋莎抱进了怀抱里。
还有一只鹰。
父亲很喜欢鹰,甚至给我取名就叫做“志鹰”,我很不喜欢这名字,经常被误会为“志英”,很女人味,我家里挂满雄鹰主题画儿,画面都很老土,这一回,我可算找到够档次的画儿了,不过,我始终没明白,自己到底喜欢这画上的鹰还是女孩。
没想到的是,那女孩,真的就叫做喀秋莎。
喀秋莎(二)
更没想到的是,回到桂林收到的第一个消息,竟然是父亲住院了……我那体壮如牛的老爸,也会住院?
我没来得及放下行李,直接奔老干部医院。妈妈在医院门口等我。
“前天早上,你爸发现尿血,医院拍片,发现膀胱有个瘤子,但他说什么也不肯做手术。”妈妈说:“你哥哥姐姐都回来了,谁也劝说不了他,看你的了。”
“志鹰康帕雷斯,你回来了?快,来给我讲讲你的莫斯科之行。”
我很小就知道,所谓“康帕雷斯”,就是俄语“同志”,这趟莫斯科之旅我才知道,退役空军大校张正义同志的俄语很不标准。不过,嗓音依旧洪亮若黄钟大吕,完全不像大病卧床的七十三岁老人。
我放下行李,给我家老首长敬了个军礼。
“我不做手术!国民党加美国鬼子都没敢给我挂彩,都这把年纪了,还让自己人给我来个开膛破肚?”
我扑哧一下乐了,刚才的紧张焦虑顿时被冲跑了一半。“得了吧,老爸,您那是人家不敢打你吗?您不是没捞着上前线的资格不是?”
父亲十六岁参军,给首长做了两年警卫员,就被送到苏联学习,学习结束后就回内地修理飞机,连鸭绿江都没跨过。
“臭小子,敢揭老子短?快,坐下,给我讲讲莫斯科。”
看来,不汇报完旅行工作,首长是不会听完关于动手术与否的利弊论证报告的。
我向老爸呈上一本《俄罗斯旅行手册》,然后指点画面,将自己二十多天来,游览俄罗斯大地的种种见闻详细的做了一次汇报,听得老妈直打哈欠。
老爸见状,就势把我妈打发走了。
老妈一走,老爸就压低嗓子问我:
“说说,苏联姑娘漂亮吗?”他还是接受不了苏联解体这个事实。
我笑了,原来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难怪我那么好色。
“喏,我带了一位苏联‘玛达姆’(准俄语,美女的意思)给您瞧。”我指指行李,那幅油画用牛皮纸包扎着。
“什么玩意儿,一幅油画吧?打开我看看。”老头儿好奇心还挺强。
牛皮纸层层打开,当那女孩的形象出现在老爸眼前时,老爸一下怔住了,眼睛里霎时间闪现出与年龄极不协调的光芒。
“喀秋莎!”老爸惊呼一声,“她,她就是喀秋莎.斯韦特拉娜,这画儿画的是喀秋莎,那只鹰的名字叫波克雷什金,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波克雷什金,它受伤了,翅膀那儿,扎着绷带,看见没?”
我将信将疑,靠近油画仔细一看,真的,老鹰翅膀羽毛下面依稀可见白纱布痕迹。
我糊涂了,不会有这么巧的事吧?
“爸爸,您,您以前见过这幅画儿?”
“不,没见过……志鹰,你也累了,先回家休息,明早早点来,画儿先给我留下,去吧。”
我习惯了这老头说一不二的风格,没敢多废话,转身离开了医院。
喀秋莎(四)
“离开学校时,喀秋莎没来送我,汽车开到大门外,我看见她站在路边,向我挥手,手上还举着一根羽毛,我知道,那是波克雷什金留下的一根翅膀毛,也许她想送给我,但来不及了。
过去我曾隐约听妈妈说过,我父亲后来升职慢的主要原因是,组织上怀疑他和苏修特务谈过恋爱。
父亲喝了一口水,平静了一会儿,然后指指那幅画,说,昨晚,我突然想明白了事情的全部真相。
“安德烈也喜欢喀秋莎,他会画画儿,总是以画画的名义接近喀秋莎,不料,喀秋莎可以向他展示裸体,但不愿意展开双臂,见我居然与喀秋莎抱在一起,当然不服,于是利用职务之便,报复了我。”
“您是说,我买到这幅油画,就是当年安德烈为喀秋莎画的画儿?不会那么巧吧?再说,安德烈为喀秋莎画画时,还没有那只鹰啊。”
“我忘了说,喀秋莎也会画画儿,没准是她后来自己把波克雷什金画上去的。喀秋莎是乌克兰草原上长大的姑娘,特别钟爱雄鹰。我字基辅学习时,还收到她一封信,信中有一句话我至今还记得,也常给你说,知道是什么吗?”
“……鹰有时飞得比鸡低,但是鸡永远飞不了鹰那么高。”
“对,好小子,还行,老爸没白教你……对了,通知医院,安排手术吧,管他是恶性还是良性,是肿瘤老子就不让它在我身上待。”
我鼻子一酸,笑了。
“这画你拿到你自己住处挂去,别让你妈看见……在我家墙上挂个光屁股女人,你妈非疯掉不可,哈哈。”
说完,老爷子往枕头上一靠,说:“去,给老子找点吃的来。”然后戴上老花镜,翻开一本书看了起来,是我昨天拿回那本《俄罗斯游览手册》。
我突然发现书里多了个奇怪的东西,过去仔细一看,居然是一根羽毛,而且,决不是鸡毛。老爸把他夹在书页里当书签用。
“这羽毛哪儿来的?”我问。
“呵呵……”老爸笑得有点狡猾,“不告诉你。”他说。
三天后,老爸手术成功,肿瘤切片结果为良性。
直到这时,我才有心情回到自己住处,整理莫斯科之行带回的行李,当我把那幅《喀秋莎》挂到墙上后,猛然发现一件绝对灵异的事情。
喀秋莎端坐在钢琴边,钢琴上空空如也,那只老鹰不见了。
我打开MP3,歌声响彻我的小屋。
“正当梨花开遍了天涯,河上飘着柔漫的轻纱,喀秋莎站在竣峭的岸上,歌声好像明媚的春光;姑娘唱着美妙的歌曲,她在歌唱草原的雄鹰,她在歌唱心爱的人儿……她还藏着爱人的书信……喀秋莎爱情永远属于他!” (散客月下2008-5-6 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