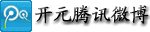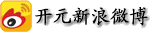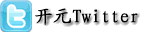日志
西边的太阳
热度 8
西边的太阳
以往都是在九月底回国的,这次为了跟埃蒂的旅行“接轨”,一定要在月初就守在京城,迎接那辆东方列车。
“秋老虎”的尾巴也耀武扬威地等着我,扫的我发懵。
那个旅行团的最后一站是北京,两天半的时间里团员们自由活动,我想:怎样才能带她们逛更多的地方?
我三十多年不见的小学同学在校庆上遇着时一下抱住我,我说你还挺西化的,她说不是不是,我从来不这样的,不知为什么忽然就觉得特别亲。
“特别亲”同学知道了我的来龙去脉,坚持不让我放弃颐和园,说可以一早接我们去,午后把我们送回故宫,再去忙她的,现如今还有这事儿?不是说商品社会都人情冷漠了吗?这简直就像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嘛。
她还给我找来一张介绍信,凭它去北京的公园,四处平蹚,只在景山进门时见收票嘟哝了一句:“没说有老外呀。”
是啊,老外“那么有钱”,凭什么享受我们国人的优惠?我领着埃蒂和她的朋友玛格丽特又砍价又刷公交卡的,到处遇见同胞狐疑的目光,不管那些,只要她们不停地惊异“真便宜真便宜”我就觉得特自豪——瞧瞧咱北京,啊(发二声),哪儿像你们德国……
从北海出来时天色已晚,我问二位想吃点什么,埃迪说饭不重要就想赶紧坐下来,快累死了。
我挺实在的就带她们冲进了最近的一家包子铺,晚餐吃得像早点,两笼包子三碗馄饨,她们居然还赞不绝口,夸那馄饨皮“ganz dunn”,不敢恭维的是小店的卫生,老板娘被我带进来的人吓了一跳,我们刚坐下她就马上站起来擦桌子,挨个儿擦,边擦边往这边瞟,我问:“你这儿没来过老外吧?”得到肯定后她更使劲地擦那些桌子。
我们走时她的眼神还没缓过来,满是“今个儿太阳打哪边出来?”的疑问。
我煞费苦心的安排最后功亏一篑,省了半天的钱以几倍的数额又还给了北京,玛格丽特丢了她的包,幸好里面没有护照,不然我该急疯了,也幸好受损的不是埃蒂。
我给那家餐馆留了电话,希望有下落与我联络,不过是安慰她们罢了,心里知道,若能找回来那太阳才真是从西边出来了呢。
北京给埃蒂的美好超出了她的预料,回去便说以后还来,还要去中国南部,尽管我们是那么好,我还是在心里叹了一句:您饶了我吧。
我和埃蒂的关系很多文章里都有提到,挂上新发表的这篇,诸位了解一下吧。
流星划过的夜晚
驱车前往新城(Neun Stadt)的路上,暮色渐浓,乡间的景致在清幽中氤氲着朦胧的雾了,愈晚愈显出一种无法解释的神秘。
晚风柔和。
从古堡门洞似的入口走进剧场,柔和的风仍在四下低徊,我望望“屋顶”:还从未见过如此巨大的“帐篷”,灯光从后上方打过来,越过座“皆”虚席的剧场,照向舞台。
舞台没有幕布,台上的布景依山而设,几幕的场景都布置在这一方天地,在后来观看时才发现它们随剧情转换时被利用的自然和巧妙。
演员们正在排练,导演指挥着他们在唱剧中的民歌,一曲终了,很多人都过来和埃蒂握手拥抱,亲热寒暄,也礼貌地向我伸手,使我觉得这些人很随和。
埃蒂认识许多演艺界的人,有时我俩在一起看电视时,她就会指着其中的某位对我说:这人很好,跟她是朋友,以前也是剧院的演员,现在演了电视剧……
作为Haus Frau的她也是几家剧院的业余裁缝,一辈子的临时工作就是做戏服改戏服熨烫整理修补加工之类,有时会把“活儿”拿回家干,就在上午,我还不失时机地挑了两件“行头”假装十八世纪的贵妇,提拎着大裙子满屋转,把她家当影楼了。
搔首弄姿时只听后面“嘶”的一声,不赖我撑得哦,咱虽够胖,那些拖拖拉拉的礼服钻进去还是有富余的,是埃蒂在后面别了别针,可怜已有三十余年的戏装表面光鲜,禁不得一拽就开了裂,埃蒂没听见,我当然也不会说了,拍够了坦然地挂好。
现在我们来看戏,准确地说是来看一场公演前的彩排,整个剧场里只有不多的工作人员和他们带来的亲友,细碎的夜色滤过“屋顶”的边缘,泻下阵阵凉意。
剧情讲的是一位德国青年到匈牙利度假时与一位乡间女孩短暂的爱情故事,话剧就叫那女孩的名字,后来看报上的报道,剧名居然写的也是“匈文”一长串字母上还有一些“撇”,怎么他们不按谐音来翻译呢?像我们的《哈姆雷特》之类,难怪埃蒂只跟我说了一遍那剧名就不说了,我再问时,她居然说是她瞎说的,真莫名其妙。
我很佩服演员们的功底,因为这个晚间的露天剧场,我穿了三件衣服还忍不住发抖,不是我冷,是我看着他们冷,看他们短衫短裙的夏装替他们打哆嗦,而他们的表演自始至终都像在盛夏一样,那种阳光下的慵懒和惬意,天哪,躺在雨后的风里怎么做得出来。
有一幕表现乡村的早晨,换景时一位老妇人赶着一群鹅从舞台前经过,后面跟着个拿树枝的男孩,鹅是真的,摇摇摆摆过来时,看台上有只亲友抱来的小狗开始狂吠,且越叫越响,就在我身后的导演终于忍不住令那人管狗,不喊还好,被捂了嘴的狗挣扎着发出一阵好笑的呜呜声,鹅阵有些乱了……可演员们没一个分神的,他们就在剧情里,包括那个七八岁的儿童,那定力,直让人想到德——意志。
戏的尾声,女主角独自来到站台望着火车远去的方向,乡下姑娘眼中复杂的离伤不禁让剧场里响起我清冷的掌声。
埃蒂忙按我的手,我知道我的掌鼓得早了几秒,演员要表达的内心还未到淋漓尽致的极处,但我已经怕了,我怕再看那双眼睛,我想打断那种流露。
她的魅力犹如闪电劈开我内心的时空,观戏人已不知台下的自己身是客了……
还好,稀疏的掌声跟着从不同处响起,坐在我后面的导演大声指挥着谢幕,先是其它演员上场鞠躬,中间留有三个人的空间,然后是男主角和女配角过来再次鼓掌鞠躬,最后女主角才跑到正中的位置,全体谢幕达到高潮,像面对满场观众一样。
望着他们,我忽然觉得自己好像国内文化部门审戏的领导——对创作很有生杀权的那种,所以舞台上的人们不敢怠慢……
可现在的我,是在人生过半的某个夜晚,偶然的沉浸在异国他乡一场权作为自己上演的戏中,想着曾经的岁月蹉跎……
假设,若真有这两种选择让此生重来?
不可思议,我倾向的还是显然“艰辛”的后者。
回来的路上埃蒂给我解释剧情,我居然很傻的问了一句:“后来呢?”她很夸张地做了个“我怎么知道”的动作,手都离开了方向盘。
戏散了,人还在故事里,这不能不“怨”演员们高超的演技,当埃蒂告诉我除了老板和导演,剧中所有的演员都是业余的话剧爱好者时,我的心在空旷的夜色里陡然一震,然后我看到了流星,仿佛上天欲言又止的眼神,匆匆地掠过黑暗,不会那么巧吧?难道就因为流星是心愿的象征,我便以为我看见了它吗?
我想,如果一个人心中的迷恋也正是他所从事的职业,那这人无疑是抓到了命运的“上上签”,但这样的幸运者毕竟不多,更多人的生命都是与梦想无缘的,生存的现状总是在迫人不断地放弃 、放弃、再放弃!能不计报酬地沉浸其中,除了牺牲精神,前提当然是衣食无忧。
然后便在这无忧里纵情自己的爱好,如果我们此时再想到命运,那不是命运给了这些人略次点儿的“中吉”之类,而是命运把他们安排在了可以如此完成这样一个心愿的社会
只要那心愿在生命里真实的亮过,即便一闪即逝,即便不留痕迹……
我忽然非常的羡慕他们了,尽管这个世界上令人动心的“羡慕”很多,并一向只令我漠然。
发表评论 评论 (15 个评论)

- 回复 紫色心情
- jong: 读嫩的文章, 我的感觉和嫩的小学同学一样, 感觉特别亲, 呵呵. 虽然咱们还素未谋面.有机会就好,听说这活儿挺来钱的。

情景剧流行的时候, 要是有机会, 嫩说不定还能当个不错的编剧哟. 瞧,还没操刀就已经杀气腾腾了。
瞧,还没操刀就已经杀气腾腾了。

- 回复 紫色心情
- jong: 高中的时候, 特别迷恋话剧, 特别喜欢雷雨, 茶馆, 原野. 还特爱背剧里的台词, 呵呵. 唉, 后来还是被家长扼杀了.唉——,我也替高中时的嫩叹一声。

少年时的话剧爱好被“扼杀”了,现在就在国剧里频频换装,过过当年的戏瘾吧。
人生也如戏,愿嫩的舞台精彩。

- 回复 jong
- 紫色心情: 唉——,我也替高中时的嫩叹一声。本来想假模假式地演一下舞台大剧, 现在只能老老实实地扮自己的人生小戏,少了些许乐趣啊。呵呵。
少年时的话剧爱好被“扼杀”了,现在就在国剧里频频换装,过过当年的戏瘾吧。
人生也如戏,愿嫩的舞台精彩。

- 回复 紫色心情
- jong: 既然是特别亲, 就不会杀气腾腾。拿着刀也就比划比划。倒是小心切着自己的手。我完了,让嫩说的连“比划”的资格都没了,现在两手空空的,好不失落啊。

 ,别以为这眼泪哗哗的是切手了啊。
,别以为这眼泪哗哗的是切手了啊。

- 回复 紫色心情
- jong: 本来想假模假式地演一下舞台大剧, 现在只能老老实实地扮自己的人生小戏,少了些许乐趣啊。呵呵。噯,嫩的“人生小戏”是怎样的?可否说来听听?

我总这样“不失时机”地打探人家可真是不好,好奇害死猫啊,道理虽明白,可还总是见空儿就想试试,嫩既然亲的像我的小学同学,帮帮咱,这便如何是好? ,这个表情比较接近无奈。
,这个表情比较接近无奈。

- 回复 jong
- 紫色心情: 噯,嫩的“人生小戏”是怎样的?可否说来听听?嫩对我好奇, 真是我的荣幸, 证明嫩对我青眼有加, 呵呵.
我总这样“不失时机”地打探人家可真是不好,好奇害死猫啊,道理虽明白,可还总是见空儿就想试试,嫩既然亲的像我的小学同
嫩见过京剧舞台上跑龙套的吧, 一会儿打旗儿, 一会儿耍刀, 一会儿翻跟头, 累得汗如雨下, 忙得不亦乐乎. 可是观众不会正眼瞧你,更不会念叨你. 这是舞台上的小戏.
人生如戏, 戏如人生. 这句话这两天我好像一直在念叨.
我的人生小戏亦是如此, 呵呵.

- 回复 紫色心情
- jong: 嫩对我好奇, 真是我的荣幸, 证明嫩对我青眼有加, 呵呵.“证明嫩对我青眼有价”?我的眼睛有青了吗?现在赶快照照镜子,看是不是不小心被又打旗儿,又耍刀,又翻跟头的人的碰着了。

嫩见过京剧舞台上跑龙套的吧, 一会儿打旗儿, 一会儿耍刀, 一会儿翻跟头, 累得汗如雨下, 忙得不
这么忙累的人,还能如此关注,感动得我眼睛都红了,真的,是红不是青。
到了幕后,好好地睡一觉吧,祝嫩做个好梦。